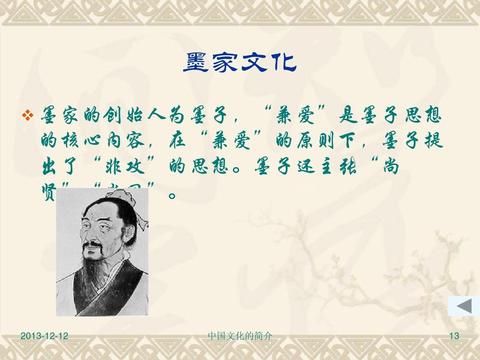
在钢筋水泥构筑的现代都市里,电梯间的点头之交、外卖员与顾客的匆匆对话、社区群里“求借一把葱”的临时互助,这些碎片化的人际互动中,总藏着一个古老的追问:当血缘纽带被稀释、熟人社会被解构,我们该如何重建跨越差异的互助精神?两千年前,墨子与儒家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答案——前者以“兼爱”破“别爱”,主张无差别地拥抱所有人;后者以“推己及人”立“仁本”,强调由近及远的情感延伸。这两种思想如同两面镜子,既照见了传统伦理的深层结构,也为当代社会的互助困境提供了破局的智慧。
一、“兼爱”与“推己及人”:两种互助伦理的源起与张力
墨子的“兼爱”思想,是对春秋战国时期“强之劫弱,众之暴寡”(《墨子·兼爱中》)现实的激烈回应。他认为,社会乱象的根源在于“别相恶”——人们以血缘、阶层、地域为界,将他人视为“异己”。因此,他提出“兼以易别”,主张“视人之国若视其国,视人之家若视其家,视人之身若视其身”(《墨子·兼爱中》)。这种“无差等”的爱,本质上是一种超越具体关系的普遍性伦理:爱陌生人如同爱家人,助他人如同助自己。墨子甚至以“交相利”论证其可行性——当每个人都主动付出爱与帮助,最终会形成“爱人者必见爱也,而恶人者必见恶也”(《墨子·兼爱下》)的良性循环。
与墨子的“兼爱”不同,儒家的“推己及人”建立在“差序格局”的伦理基础上。孔子说“夫仁者,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(《论语·雍也》),孟子进一步阐释为“老吾老,以及人之老;幼吾幼,以及人之幼”(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)。这种“由己及人”的逻辑,以“亲亲”为起点,通过情感的“推扩”实现互助的延伸。它承认人的情感天然有亲疏远近——对父母的爱最浓烈,对朋友次之,对陌生人更淡,但强调这种情感不应被固化为冷漠的壁垒,而应像涟漪一样向外扩散。正如朱熹在《四书章句集注》中所言:“推己及物,其施不穷”,互助的动力源于“将心比心”的共情,而非抽象的道德命令。
两种思想的张力,本质上是“普遍性”与“具体性”的冲突。墨子的“兼爱”如同一张覆盖所有人的伦理大网,却因缺乏情感根基而常被批评为“薄于亲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;儒家的“推己及人”则扎根于具体的人际关系,却可能因过度强调差序而陷入“爱有等差”的局限。但这种张力恰恰构成了传统互助伦理的完整光谱——前者提供了超越性的价值导向,后者奠定了实践性的情感基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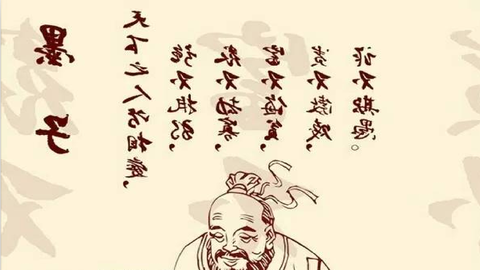
二、当代社会的互助困境:原子化与工具化的双重挑战
当我们将视角转向当代社会,会发现互助精神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一方面,现代社会的“原子化”趋势削弱了互助的情感纽带。城市化、个体化进程让人们从“熟人社会”进入“陌生人社会”,传统的宗族、邻里关系被解构,个体更依赖自我实现而非群体互助。数据显示,中国独居人口已超1亿,社区中“对面不相识”的现象普遍存在(国家统计局,2022)。这种物理与心理的双重疏离,使得“兼爱”所需的“视人如己”缺乏现实土壤。
另一方面,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互助的“动机异化”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,人际互动常被简化为利益交换,互助行为可能被解读为“投资”或“算计”。例如,职场中的“帮忙”可能隐含着“未来回报”的期待,网络上的“爱心捐赠”可能因信息不透明而引发信任危机。这种工具化倾向,让儒家“推己及人”的纯粹共情变得稀缺——当互助被赋予太多附加意义,其本身的伦理价值反而被遮蔽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,两种传统思想的优势在当代被片面放大。有人以“兼爱”之名倡导无差别互助,却忽视了具体情境中的情感联结(如对陌生人的过度干预可能侵犯隐私);有人以“推己及人”为据固守小圈子互助,却拒绝向更广泛的群体延伸(如对弱势群体的冷漠)。这种割裂,恰恰暴露了当代互助精神的“精神贫血”。
三、融合与重构:传统智慧对当代互助的启示
面对困境,传统思想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现成答案,而在于提供“融合性”的思维框架。墨子的“兼爱”与儒家的“推己及人”,本就存在互补的可能——前者为互助提供“普遍性”的价值锚点,后者为互助注入“具体性”的情感动力。这种融合,或许能为当代互助精神的重构提供三条路径:
其一,以“推己及人”培育互助的“情感起点”。儒家强调“亲亲而仁民”,提示我们互助应从可感知的具体关系出发。例如,社区可以通过“邻里节”“共享厨房”等活动,让居民在共同做饭、维修、育儿中建立情感联结,将“陌生人”转化为“熟悉的他者”。这种基于具体互动的情感积累,正是“兼爱”落地的现实基础——当人们对邻居产生共情,才可能进一步关心社区里的独居老人或外来务工者。
其二,以“兼爱”拓展互助的“价值边界”。墨子的“无差等”理念,要求我们超越“熟人圈”的局限,将互助对象扩展至更广泛的群体。例如,近年来兴起的“时间银行”互助模式,鼓励人们为陌生人提供服务并存储“时间币”,未来可兑换他人的服务。这种模式既保留了“互助互惠”的现实逻辑(符合“交相利”),又通过制度设计突破了血缘与地域限制(符合“兼爱”),本质上是传统思想与现代机制的巧妙结合。
其三,以“义利之辨”平衡互助的“动机纯粹性”。墨子主张“兼相爱,交相利”,并不否定利益,而是强调“利人即利己”;儒家则强调“义以为上”,反对将互助异化为功利计算。当代社会需要的,是在“义”与“利”之间找到平衡点——既承认互助可能带来的情感满足或现实回报(如社区积分、社会荣誉),又通过教育与文化引导,让“将心比心”的共情成为更根本的动力。例如,公益组织可以通过“故事分享会”让参与者讲述被帮助的经历,唤醒内心的“恻隐之心”(孟子语),而非仅强调“做公益有好处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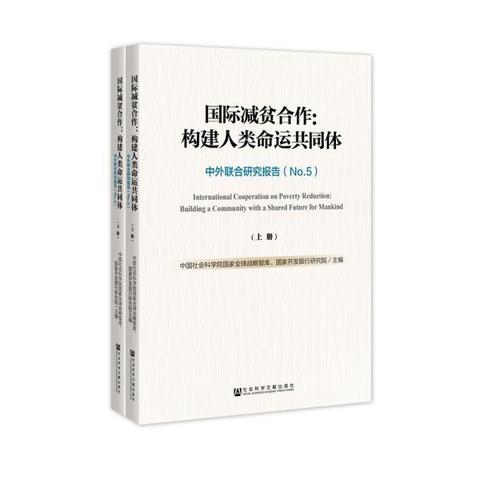
结语: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重筑互助之桥
从墨子的“兼爱”到儒家的“推己及人”,传统思想从未远离我们的生活。它们如同两条并行的河流,一条奔涌着超越性的理想,一条流淌着具体性的智慧,最终都汇入“互助”这一人类共通的精神海洋。在当代社会,我们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,而是将两种思想的精髓融合——以“推己及人”滋养互助的情感根基,以“兼爱”拓展互助的价值边界,让互助既“有温度”又“有广度”。
或许,真正的互助精神,就藏在社区里一碗热汤的传递中,在陌生人危难时伸出的手臂里,在每一次“将心比心”的共情与“无差别”的善意里。当传统智慧与现代生活相遇,我们终能重筑那座跨越差异的互助之桥,让社会在温暖的联结中更具韧性。
参考资料
《墨子·兼爱》《论语·雍也》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《四书章句集注》(朱熹)
国家统计局. 2022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[M]. 北京: 中国统计出版社, 2022.
【原创不易】转载交流请联系玄门之光




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