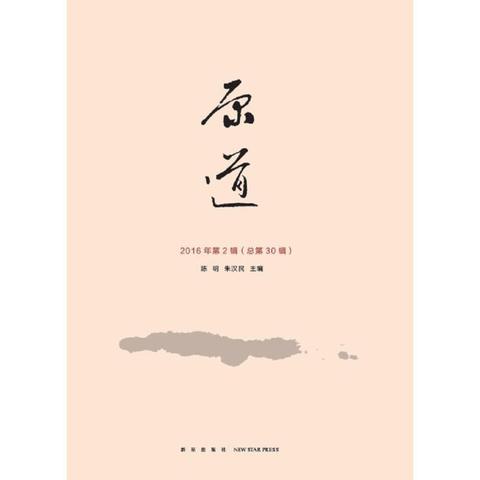
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坐标系中,“道”始终是一个核心命题。它既被描述为“独立而不改,周行而不殆”(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五章)的永恒存在,又被视为“变动不居,周流六虚”(《易传·系辞下》)的动态过程。这种看似矛盾的属性,实则构成了中国哲学对宇宙本质的深刻洞见——永恒性是道的本体特质,变化性是道的显现方式,二者在“体用不二”的逻辑中实现统一。
在中国哲学中,“道”的永恒性首先指向其超越性。《道德经》开篇即言“道可道,非常道”,这里的“常道”便是那不可言说、不受时空限制的本体。它“先天地生”(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五章),不依赖任何具体事物而存在,却又是一切存在的根源。正如王弼在《老子注》中所言:“道者,无之称也,无不通也,无不由也。”这种“无”并非空无,而是超越了具体形质的永恒本体,是宇宙万物的“第一因”。
这种永恒性也体现在“道”的不变性上。《庄子·知北游》中,东郭子问庄子“道恶乎在”,庄子回答“无所不在”,从蝼蚁到稊稗,从瓦甓到屎溺,看似荒诞的列举,实则揭示了道的普遍性——它不会因具体事物的生灭而改变,始终保持着自身的本质。正如郭象在《庄子注》中解释的:“道无不在,故所在皆通。”道的永恒性不是孤立的“永恒”,而是存在于一切变化之中的“不变”。

道的变化性源于其“生”的本质。《道德经》第四十二章说:“道生一,一生二,二生三,三生万物。”这里的“生”不是机械的创造,而是一种动态的生成过程。道通过自身的“反”(《道德经》第四十章:“反者道之动”)实现变化:向相反的方向运动,却又回归自身,从而推动万物的生长、发展与消亡。
这种变化性在《易传》中得到了更系统的阐述。《易传·系辞上》说:“一阴一阳之谓道,继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。”阴阳二气的相互作用是道的具体显现,而这种作用是永恒的、不间断的。“日新之谓盛德,生生之谓易”(《易传·系辞上》),道的变化不是混乱的,而是遵循着“理”(规律)的,这种“理”是永恒的,而变化是“理”的体现。
道的永恒性与变化性并非对立,而是体用不二的关系。“体”是道的本体,是永恒的、不变的;“用”是道的作用,是变化的、显现的。正如程颐所说:“体用一源,显微无间”(《程氏易传·序》),体是用的根源,用是体的显现,二者不可分割。
在道教中,这种统一表现为“道法自然”(《道德经》第二十五章)。“自然”不是指自然界,而是指道的自身本性。道的永恒性是“自然”的,变化性也是“自然”的,二者都是道的本性的体现。庄子的“逍遥游”正是这种统一的最高境界:通过“无待”(超越对外在事物的依赖),达到“与道合一”的状态,在永恒中体验变化,在变化中把握永恒。
在佛教中,虽然“道”的概念与道教不同,但也有类似的思想。例如,大乘起信论中的“真如缘起”说:真如是永恒的、不变的本体,而缘起是变化的、显现的现象,真如通过缘起显现自身,缘起是真如的作用。这种“真如”与“缘起”的关系,与道教的“体用不二”逻辑异曲同工,都强调永恒与变化的统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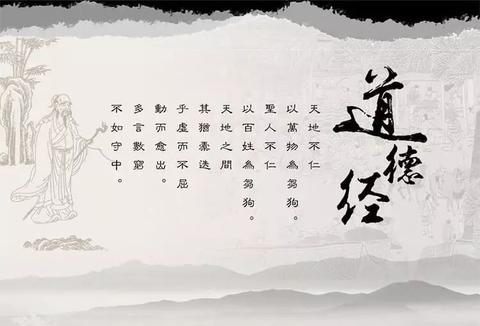
道的永恒性与变化性的统一,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,我们常常面临“变”与“不变”的困惑:一方面,科技的发展、社会的进步让一切都在变化;另一方面,我们又渴望有一些永恒的东西,比如道德、亲情、信仰。
从道的哲学来看,这种困惑其实是不必要的。因为“变”是永恒的,而“不变”的是道的本质——那些支撑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,比如善良、诚信、责任,都是道的体现,是永恒的。我们需要做的,是在变化中坚守这些永恒的价值,在永恒中适应变化。正如《论语》中所说:“君子务本,本立而道生”(《论语·学而》),只要抓住了“本”(道的本质),就能在变化中保持清醒,在永恒中实现自我。
道的永恒与变化的统一,不仅是一种哲学思辨,更是一种生活智慧。它告诉我们:世界是变化的,但变化中蕴含着永恒;人生是短暂的,但短暂中可以体现永恒。只要我们把握了道的本质,就能在变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位置,实现生命的价值。
【原创不易】转载交流请联系玄门之光











